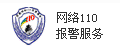我想先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个主题演讲,后一个半小时我很想和同学们进行不拘一格的交谈。我这个讲演的题目是:“你是否要预知今生的苦难”,这题目有点吓人。
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,是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一次谈话的题目。当时是在餐桌上,讨论得特别激烈。大约有一半人说他们非常想知道他们今生将要遭遇什么样的苦难。还有一半人说他们不想知道。我属于不想知道的那一派。为什么?因为首先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达到的。我们没有办法来预知今生会有哪些苦难。比如说刘海洋(近日“硫酸泼黑熊”事件的主角——编者注)。那天我问几个同学,你们说刘海洋苦不苦,有人说苦,有人说不苦。刘海洋五十六天的时候父母分居。刘海洋今年21岁,20年前中国的产假只有56天。我猜想,刘海洋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,他父母之间就开始了争论。这种状态下孕育的胎儿,能说是幸福的吗?他出生不久,父母就分居,3岁的时候正式离婚。在他的童年,他连窗户都不能靠近,相与为伴的只是一篮积木和拼图。五六岁开始上学,人家欺侮他,骂他,他都不知道那些骂人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后来直到他报考清华大学,他填写的是生物专业,他妈给他改成计算机,他改了回去,他妈又给他改回来,当他再想改的时候,他妈说你要再改我就把志愿表撕掉。我也是做母亲的,我认为刘海洋母亲这一招挺凶的,够厉害的,给刘海洋造成的压力也是巨大的。这样的苦难他能否预知?技术上做不到。
但是人生一定是会有苦难的,我们无法预知。越是你有一个抱负,有一个理想,承担很多很多的责任,要去建立常人所未曾建立的功勋,我觉得,你就越要做好准备,遭遇到比常人更多的苦难。而且是很孤独的。但我觉得,如果我们从年轻时开始准备,建设那样一个“防护林带”,就可以决定我们如何对待苦难的态度。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,像遇到癌症这样的生死威胁的时候,其实这苦难的核心是一个哲学的问题,就是我们人是有一个大限在等着我们,无论你多么年轻,无论科技怎样发达,无论你怎样气壮山河,无论你有多少爱与被爱,那个大限就在那里等着我们。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,才使我们的生命变得那样宝贵,才使我们要决定,用这有限的生命,一步步的走过去,当我们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时候,我们会留下什么。
有一天晚上,夜里两点钟,突然电话铃响了,吓得我一激灵,一定有像死了人一样重要的问题,否则不应该在两点钟给人打电话。吓得我……(同学中有手机铃声骤然响起,演讲者和同学都大笑),我糊里糊涂把电话拿起来,一听是我儿子。他正在外出差,他告诉我说,妈,我特感谢你。我心里说,就是感谢也不能半夜两点钟就急着打电话。我问,你感谢我什么呀?他说我感谢你有一天和我谈了人生。我想,他在几千里远的地方,他可能面对着满天星斗,想到了人生这个问题。其实人生,我觉得,还是你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想一想。尽管我们每天都很忙碌,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,但是只要你花时间想一想,它可以给你节约出很多时间。只要把你人生的目的想明确了,一些重大的问题,非常重大的问题,五分钟内就可以决定。(略……)格非:现在请大家提问。
■苦难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动力。并非苦难越多,动力越强一男生:对于人生有不同的态度,有的很开心很随意,不做思考;有的对宇宙,对生命的意义进行很深奥的探讨,比如尼采,但是不见得有很好的结果,有的精神分裂了。我想知道,你是否在一个特定的时间,特定的地点,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过这样的思考,然后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?
毕淑敏在清华的演讲:预知今生的苦难毕淑敏:我先把这本书签了字送给这位同学。(同学笑)这个同学的问题是我怎么看人生,是吧?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规定有个人生的意义,不是书本上教给我们的,不是父母给我们的,而是你自己思考得出来的。对我个人来说,我会用我的生命去做我所热爱的事情,而这件事不但对我是快乐的,而且对人类是有所帮助的。我想就是这样。它说起来比较大,比较空洞,但落实起来……比如说有人让我写电视剧,但不是我喜欢的,就把它拒绝了。所以我认为,因为有了大的目标,一些小的事情,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。
一女生:我想知道你对苦难的态度。我还想知道,你为什么把你的新书的首发式放在清华。
毕淑敏:我觉得苦难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动力。并非苦难越多,动力越强。苦难究竟会转化为什么东西,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它。在苦难面前,是把它化作动力,还是把它当做一种借口,甚至因此得出人性恶的结论,去报复这个社会——我在遭受苦难,为什么有人却是如此的幸福。怎样看这样的问题,可能需要一个积累,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式。
这个同学的第二个问题是,我为什么选择清华。我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是,我欠着清华的讲演。去年、前年,清华的学生会就邀请过我,去年我在北师大读书,没时间。前年,实际上我已经答应,但是迫近三八节的时候,我却来不了了。因为有另外一家邀请了我去演讲。虽然清华的邀请在前,但我还是答应了另外的那家邀请,我对清华做了一件背信弃义的事情。在那个特定的情形之下,我觉得那个地方比清华还重要。那个地方是北京市的女子监狱。监狱中的几百名女囚犯,在3月8日和我有一个谈话。我当时心里思想斗争也挺激烈的。我想,我一辈子见过的“坏女人”是否能有几百个。我将集中看这么多人,我想和她们谈谈我对生活的看法。她们能接受我这些看法吗?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。面对这份邀请,我觉得自己作为女性,有一份责任。我在家里想,如果我去讲演,我叫她们什么,“女士们”?好像不行。“同志们”肯定不行。最后我终于特意打电话问,称呼什么好,他们告诉我,你就称呼“姐妹们”。后来谈得还挺好。监狱里当时几百名女犯穿着淡蓝色衣服坐成一个个方块,四周边上坐的是警卫,从台上看下去,我觉得很像一块块的手绢。我跟她们说,我们来做一个游戏。一下子旁边劳改局的领导吓坏了,以为我和她们玩丢手绢的游戏呢。他事后对我说,你要知道,把几百个犯人集中到一起,我们担负着多大的责任哪。万一暴狱可怎么办呢。我说,这个游戏不必大家都活动起来,你们只需要坐在座位上,闭上你们的眼睛,听我讲。我说,我讲到哪儿,你们就随着我想到哪儿。我说你们先想,你们每个人最宝贵的五样东西是什么?我看见她们都闭着眼睛,我想她们肯定都在想。后来我问,如果你要在五样东西里舍弃一样,你舍弃什么?这样一次一次地舍弃下去,最后只留下一样,是什么?女犯人们鸦雀无声。后来我说,游戏做完了,你们最后留下的那样东西是什么,我不知道,愿意告诉别人你们就回去彼此告诉,不愿意的话你们就在心里永远保守这个秘密。但是我想,即便在这高墙之内,即便你们都触犯了刑律在这里服刑,你们最后留在心中的那一样东西,终归不应该是罪行,而应该是人世间美好的东西。
第二个理由呢,我特别想跟理工科学校的学生有一个交流。有一次我和日本笔会的朋友谈话,当时正是奥姆真理教事件沸沸扬扬的时候。他们告诉我,奥姆真理教里的那些高级的干部,全都是理工科的大学生。然后那个日本人得出结论:爱好文学的人比较地不容易犯罪。他说那些奥姆真理教的人全不爱文学,不看文学书。后来我写了篇文章,题目就是《爱好文学的人比较地不容易犯罪》,投给《北京青年报》。
■语言文字看起来很廉价,但它是我们人类所能掌握的传达心灵的最有力的武器一男生:毕作家,你是我比较喜欢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之一。有两个原因,一个是你作品里边的人文关怀,再一个就是文字干净。在今天这样一个连《十月》都刊登着粗制滥造、不知所云的文字的时代尤其难得。我想提两个问题,第一个我想知道,当作家应该怎样锤炼自己的文字功底,希望毕作家就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一下。我想这个问题是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比较关心的。第二个就是说,当代文坛什么时候能够出现真正的好作品,换言之,中国的文学如何能够走出低谷,出一些能够真正传世的给人以震撼的作品。作家应该怎么办?就这两个问题。
毕淑敏在清华的演讲:预知今生的苦难毕淑敏:谢谢那位同学对我的表扬,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。我想,对语言文字要热爱它。语言文字看起来很廉价,因为一个人可以没有房屋,没有土地,没有钱,可是他可以享用这份资源——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如此灿烂的文化。我觉得语言真的是太奇妙了,它已经成为我们人类所能掌握的传达心灵的最有力的武器了。社会不停地发展,科学不停地发展,各行各业都有一些专用的术语,但是一个作家,我们却要用汉语,来表达那些最微妙,最精彩,最美丽,最动人的情感,我觉得对于语言应该去热爱它,去研究它,去分辨它那些最精细的差别。同样的语言,为什么会在不同人的脑海里激起不同的浪花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。有一个捏面人的师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谈到他对面的热爱。什么地方的麦子磨的面最好,受多少阳光照射,什么样的土壤里生出的麦子,它磨出的面是不一样的。面里加上什么样的调料,什么样的颜色,什么样的香料,它的柔韧度,它的表现力,它的色彩,耐久性,也有差别。虽然我对面的感受,除了馒头和饼的区别,没什么更多的感觉了,但是看了这篇文章我深深地被感动。如果同学们喜欢文学,要热爱我们的语言。我们中华民族传下来这么浩瀚的文学财富,其载体就是我们的语言。
第二个问题,关于中国文学何时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送给大家。昨天王蒙先生把他的十万块奖金捐出来设了个“春天文学奖”,用来奖给30岁以下的作家,我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感动。同学们都是30岁以下,我想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说: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
■其实男人女人都孤独,人注定是孤独的——别看有人花天酒地朋友多,别看烈火烹油那样的轰轰烈烈一女生:我是电子系的学生,学电子工程。我想说,在这样一个学校里,压力还是很大的。人家学德语学法语的女生结伴去逛街的时候,我还要在这里做好多好多的题,看好多好多的书。我来这里听你的演讲,还总在想有许多作业没有完成。现在有一个说法:男人孤独便优秀,女人优秀便孤独。如果学理工科,学得很多了,是否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人?现在清华有一种说法,清华有三种人,男人、女人、女博士。现在社会上对女人的期望值非常小,不要你多么优秀,学得很好。高中的时候还能够看各种小说和各种杂志。上了清华以后就没有时间了。我现在尽全力学习,也就是能获得过得去的分数。就我现在这种状态,也就只能看看读者文摘,别的根本就没有时间看,小说和散文也没有时间看。所以我就想知道,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。还有,学理工科的学生追求人文的东西到底对他帮助有多大?
毕淑敏:感谢这位同学,我能够感到她对我的信任,对大家的信任。何况她还有那么多作业没做。我能够理解你的那些压力和恐惧。你后面提了很多问题出来,我觉得那些问号不是问我,而是在问你自己。这世界真的是有偏见,你刚才说到的那些感受,你现在感受着,你一生都将能感受到。我们不能够去决定那些东西,但你怎么样来对待,你可以做选择,然后你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,也享受你的选择给予你的自由。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更合理,希望自己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。你刚才谈到一个说法,“男人孤独便优秀,女人优秀便孤独”,我想说,其实男人女人都孤独,人注定是孤独的——别看有人花天酒地朋友多,别看烈火烹油那样的轰轰烈烈。因为每个人都很独特,必须独自面对世界所有的风霜雨雪,所以人注定是要孤独的。这种孤独会变为一种动力,也可以变为一种盾牌,一种借口。孤独是一种存在,一种中性的存在。我在美国,访问了一个临终关怀医院,就在访问期间,就在那一时刻,有一个人就死了。院长跟我说,无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有多么的热闹,他必定要一个人孤独地面对死亡,没有什么技术可以让人们成群结伙地一起分享死亡。所以,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,都要面对孤独做出选择,并且所有的选择都有正面的和负面的东西。你可以对自己说,我也要去做一个文科生。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,但是做了就要负起责任来,就是勇敢地走下去。
毕淑敏在清华的演讲:预知今生的苦难一男生:我大约是在初中二年级时看过你的有篇文章,题目是《孩子,我为什么要打你》。刚才你在演讲中还提到刘海洋,提到你的儿子深夜给你打电话,感谢你跟他谈了人生。我想知道你对家庭教育有什么看法。
毕淑敏:这个同学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。首先,我对《孩子,我为什么要打你》这篇文章的观点,现在要做重要修正,因为我想那属于家庭暴力。虽然我极少打我的孩子,但是我打过他。我现在十分惭愧,尽管已经向他道过歉了。当时这篇文章被转到《读者》上去,许多文摘也把它摘了去,所以流毒甚广。我现在重新审视,我觉得对一个孩子,一个弱势群体不能打,我现在已经尽量改正,在出所有选本的时候,都要求对这篇文章不要再选,而且对中国作家协会版权代理委员会处理版权事宜的人说,所有来商量选这篇文章的,都要阻止他们选这篇文章。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讲一点心里话,我也非常高兴。如果你们的父母因为这篇文章打过你们,我向你们诚恳道歉。
■亲人之间的沟通是很有效益的一女生:在作为医生和文学创作之间,你在选择上是否有过犹豫?我母亲也是医生,也很喜欢文学,在选择上她就犹豫不决。我也想替我母亲了解一下这个问题。
毕淑敏: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了,选择真是太痛苦了,因为我尊重医生。刚开始我是不 喜欢这个职业的,但是我后来发现医生是和生命发生最紧密的关系,病人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托付给你,那是建立血肉相连的这种联系。写作常常处于一种幻想的环境,如果写得顺手,写到夜里三点,明天早上不可能精神饱满地面对把生命的一部分交给你的人,我怕造成别人的痛苦,这是一种罪过。鲁迅没有开始进行临床,他向藤野只学了基础课。郭沫若幼时得病,有一只耳朵失聪,在临床上听不到病人的心音,所以他们在学生的时候就停止了医学实践。当我选择写作的时候,把听诊器和洗好的工作服放进柜子里的时候,禁不住潸然泪下,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开始行医。
一女生:我看到过不少你写的作品,很悲壮,也很美。但这本书(指此次带来的新书《面具后面的脸》——编者注)是否使你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有所改变?你在刚才多次提到你的家人和先生,在你的生命中,你的先生是多么重要的角色?对你的生活有什么 影响?
毕淑敏:先说这本书的题目。这是我在美国的一个艺术学校,他们让十几岁的女生做手工,让她们做一个面具。面具正面是平时给人的印象,反面是真实的你。孩子们都很投入。其中一个女孩子,我书中提到的,她的父母 都已经去世,她寄居在亲戚家,心灵受到了很大的磨难。她做的面具正面很美丽,她认为是大家平常看到她的样子,反面却充满了金属、羽毛和石子,可以看到她内心很冷淡,很绝望。没有人能看得清她的内心,这就是一种分裂的局面。精神病,医学上叫精神分裂症。如果用两种标准对待自己和他人,能量会大量地流失,这种冲突,是很危险的。我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去探索,找到自己的差距,由不和谐变为和谐。人实际上是需要面具的,这是由于社交的规矩的需要,但人的本质要真诚。每个人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和谐。
我爱人对我来说,意味着手和脚,有时会觉得是我的一部分,相依为命。
一女生:我很压抑,感到沉重,因为刚才一直都在谈苦难甚至死亡。其实我们关心的不是预知,而是如何渡过苦难。比如我很少见到父母的笑脸,我们就感到恐惧。
毕淑敏:父母为何没有笑脸呢?你考上清华他们会很高兴呀。可以通过沟通试试看。亲人之间的沟通是很有效益的。你可以试试多跟父母沟通。你跟他们讲,我多么希望看到你们的笑脸呀。看起来,只要做,也许并不那么难。我曾经和陆幼青探讨过死亡。中国把死亡定义为黑暗的,丑陋的,冰冷的,恐惧的,绝望的。我觉得应该重新推敲。国外现在有“死亡学”,它认为死亡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最后阶段,对生命的必然终结,应该有更健康、更正面的接纳。做起来不容易,包括我自己。慢慢来吧。